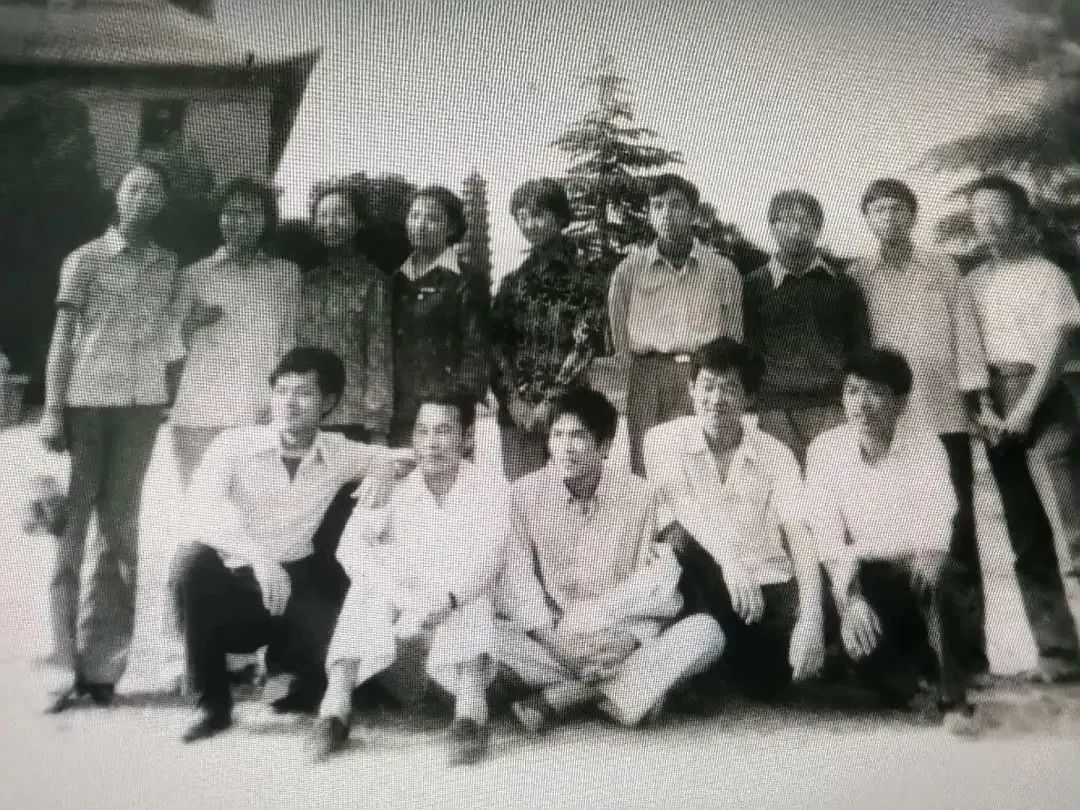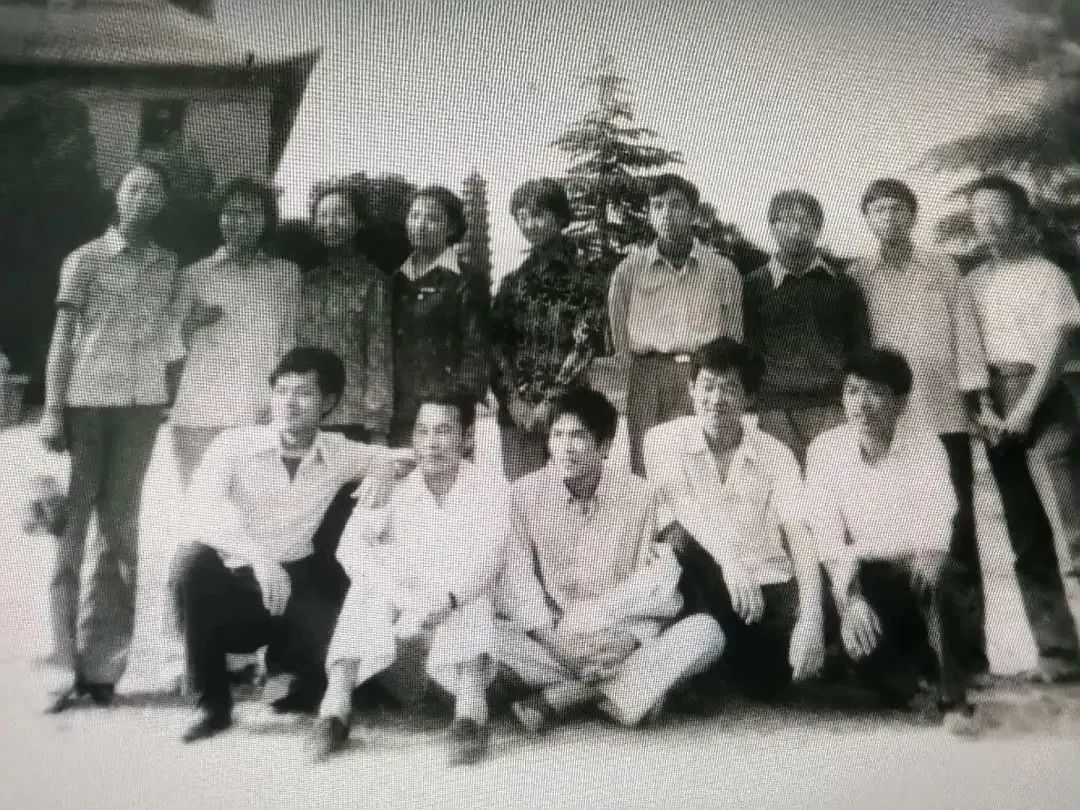高有鹏:大河大
作者:管理员 发表日期:2020-07-28 访问次数:3141
人生有许多偶然。能够读书,是人生的幸福,在什么地方,读什么样的书,总是人生的缘分。四十年前,我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,从平静的村庄来到古城开封,走进河南大学中文系,形成人生的转折。多少年来,对当年的大学读书生活有许多感慨,一直回味无穷。是啊,如果不是来到河南大学中文系,如果不是遇见这里的这样一群老师,与许多人一样,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生。 回望当年,河南大学中文系,所有的老师都值得我感谢,感谢他们传道授业,而特别难忘的是三个老师,深深影响我的学业与追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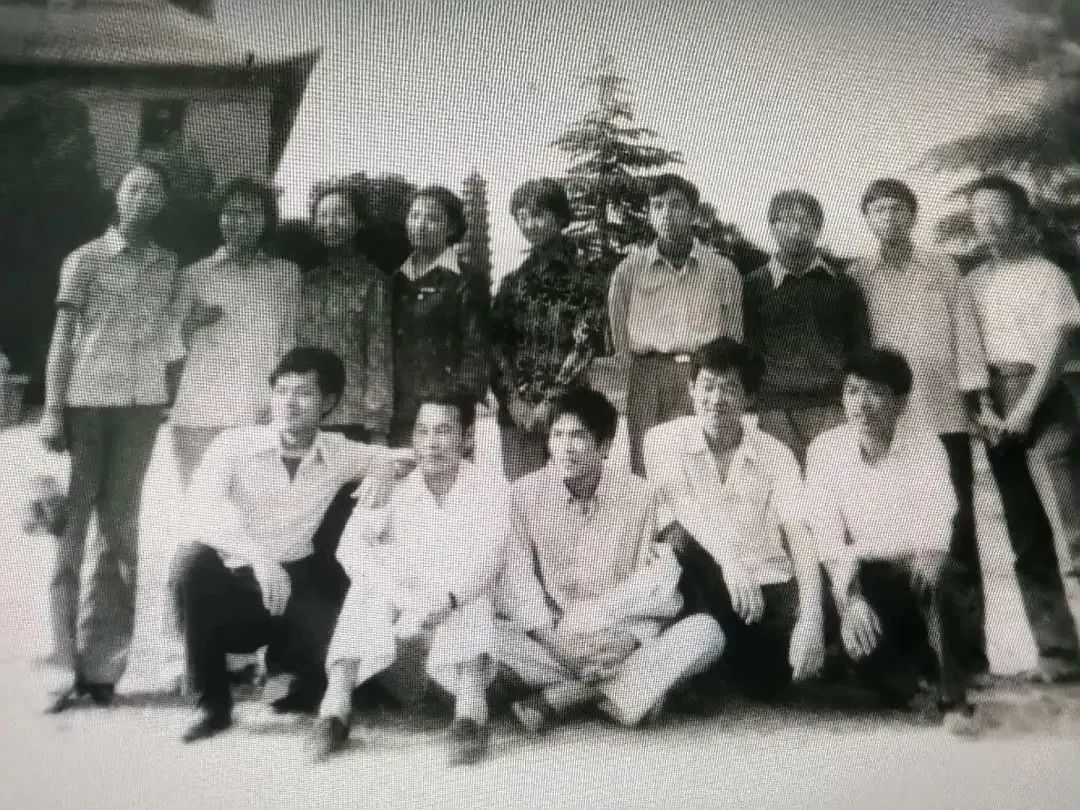
周启祥老师是一个富有情怀的诗人,每一节课都充满激情。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第一节就是周老师上的。他不是从一九四九年的文代会讲起,而是从自己的作家朋友端木蕻良写出的长篇小说《曹雪芹》讲起。他当时似乎还没有完全平反,一幅工人模样,戴着塑料壳的安全帽,发白的劳动服,每一节课结束前,他都情不自禁高喊鼓励同学们的口号。他最令人感慨的是希望同学们写出并发表作品,出现像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的作家。我在中学读书时就有作品发表,所以对周老师特别亲切,总想与他多说几句话。有一次,与同学一起去了他的新家,与他聊起,他讲起自己的经历,才知道他当年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新诗发表。他曾经是新四军的优秀战士,多次打入敌人内部策动起义,特别是四十年代,新中国成立前,他被国民党抓去就要杀掉,赶上上海解放,才被解救。他特别提到,他的经历中,非常难忘的是抗美援朝中与毛岸英的相处,他说,毛岸英也是一个富有诗情的战士,与他讲了许多苏联诗歌等等。抗美援朝结束了,周老师曾经在中央机关工作,后来想念老母亲,回到家乡,来到河南大学教书。一九五八年,他被打成右派,开除公职,在木器厂打棺材为生。在这样的环境,他仍然写诗,念念不忘心爱的文学。打倒四人帮后,周老师恢复河南大学中文系工作,所以有机会给我们讲课。当年,我写出来历史小说的初稿,让他指教,他讲了许多。经他介绍,我认识了作家姚雪垠、魏巍、苏金伞、陈雨门等人,有了后来的多卷本历史小说。后来,我与韩爱萍老师他们一起做河南文学史,又得益于周老师的许多史料。尤其是研究姚雪垠,从周老师那里得知姚雪垠对民间文学的研究,特别是他对中国射日神话的研究与书写《李自成》的关系。周老师是一个诗人,影响我们的写作。我回到河南大学中文系工作,遇到周老师病重。他的葬礼非常冷清,罕见的是由河南省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主持,周老师从四十年代就是我国局级高干。我与当时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刘进才老师等人给他写了悼词。
我们入学的第一节课,是当时河南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任访秋老师讲的。任老师高度近视,却非常有远见,他讲起中文系学生应该有大视野,做大学问。最难忘的是他从王国维和梁启超讲起,讲人生“蓦然回首”的三个境界。后来,我受张振犁先生安排做毕业论文《河南现代民间文学史》,请教任先生。他讲起自己在河南初级师范读书,他的老师白启明指导他做歌谣与谜语、谚语搜集,才有他第一篇论文研究谚语发表。他详细介绍了河南历史上的民间文学研究,从自己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开篇为五四运动中歌谣学开始,他把明代民间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夜。其他像河南历史上的乡村教育与民间文学,地方文化与民间文学等,特别是淮阳、洛阳、开封等地的学者研究民间文学,他的介绍非常有价值,打开了许多思路。其实,任先生有意延续了他的师道,有胡适、周作人、钱玄同和董作宾、白启明他们的影子。任先生的文学史研究,有古代,有近代,有现代,深深影响我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写作。当时,我非常羡慕任先生的学问,给自己起了一个叫欧阳儒秋的笔名。如今,我出版《中国民间文学史》《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》《中国民间文学通史》《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》《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史》《中国近代民间文学史》《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》等等,都有当年河南大学中文系的任先生的影响。
当时的河南大学中文系,我是从一本《河南民间故事》知道的,其署名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。入学以后才知道,这是张振犁先生编写的。 认识张振犁先生,是我人生的幸福。一九八零的冬天,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,我误入当时十号楼的一零八教室,赶上张振犁先生为高年级上课,才知道有这门课。一九八一年冬天,七八级的王剑冰学兄领着我去张振犁先生家,算是正式拜见先生。王剑冰是当时有影响的校园诗人,他的诗歌在《诗刊》上发表,“我是一辆叮叮当当的洒水车,洒一路青春”,在同学中传唱,他的剧作还获得全国大奖。他的一篇文章,写《李自成》与民间文学,选入学校科研论文集,吸引我对民间文学的兴趣。从此,张振犁先生让我参加他修订的-《河南民间故事》增订本 编写,成为他的课代表,在他的指导下,我们成立河南大学民俗学社,编印《民俗学通讯》,编写《河南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》。我们的民俗学社指导老师是张振犁先生,顾问有任访秋、于安澜、刘溶池、牛庸懋、宋景昌,还有历史系的毛健予老师。毛老师是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中学时代的老师。我们的刊物《民俗学通讯》通过毛老师寄给赵紫阳,受到赞扬。张振犁先生非常耐心地教导我读书,帮助我修改作业,有几篇论文经张老师帮助发表了,深深影响我的学业。最难忘的是,张振犁先生一字一句地帮我写出来毕业论文《河南现代民间文学史》,直接影响我后来的中国民间文学史系列。时间长了,我了解到,张振犁先生读大学的时候,一度生活困难,曾经在中国文联做过老舍与赵树理的助手,在钟敬文的鼓励下从读研究生,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生。他在大学读书时期,发表一篇民间故事的整理文章《毛主席懂得老百姓的苦楚》,选入全国小学语文课本,教育几代人。从张振犁先生那里知道,河南大学的历史与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息息相关,建校之初有德国教师教学生中国与德国民间故事,二十年代有作家郭绍虞研究谚语,罗根泽研究民歌,董作宾研究民俗与民间文学,中州大学学生白寿彝研究民歌。三十年代有江绍原做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,研究民俗与民间文学,姜亮夫研究敦煌民间文学,高亨研究神话,朱湘研究民歌。四十年代研究民间文学的更多,任访秋之外,有张遂青、朱芳圃、张长弓、邵次公等一大批,特别是丁乃通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,马可的民歌研究,在全世界产生影响。建国后,河南大学的民间文学研究,又增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研究民间文学的赵纪彬、孙作云,和研究鲁迅民间文学思想理论的汪玢玲等人。张振犁先生研究中国近代民间文学史,研究胡适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,特别是带领一批学生走遍中原大地,开创了中原神话学派。河南大学中文系,从七十年代的康保成、廖奔研究民间文学中的戏曲戏剧,孟宪明、王定翔、尉迟从泰、娄扎根、朱淑君等人研究民俗,七八级程健君、王剑冰、 陈江风、魏敏、丁晓宇和华锋等人,七九级的耿瑞、高恒忠他们,八零级的我们,包括霍清廉等人,八一级的刘炳强、郑大芝等等,都有民间文学研究著作。而且,新一代更茁壮成长。后来,我出版第一本书,扉页上写“谨以此书敬献给张振犁先生”。四十年来,我们与张振犁先生情同父子,心中永远敬爱。我每出版一本书,都会郑重送给他。最令人感动的是,张振犁先生九十五岁出版多卷本《中原神话通鉴》。他曾经获得全国民间文艺学终身成就奖。其实,他一生有多少委屈,不能完全诉说。今年一月,张振犁先生驾鹤西去,我为先生写了一幅挽联:九十七年躬耕天地,一身赤诚光耀神州。祝福先生永远安康。 河南大学历史上有一群作家,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。这与河南大学中文系息息相关。非常难忘的是,在我非常艰难的时刻,河南大学中文系是我人生温暖的港湾,我有许多话要说。我深深地祝福河南大学中文系,希望它永远安康。
(转自文学院官微《我在河大读中文》栏目)

高有鹏:历史学博士,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,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,国际书画艺术发展联合会(加拿大)副主席,美国马赫西管理大学合作导师(讲座教授)。